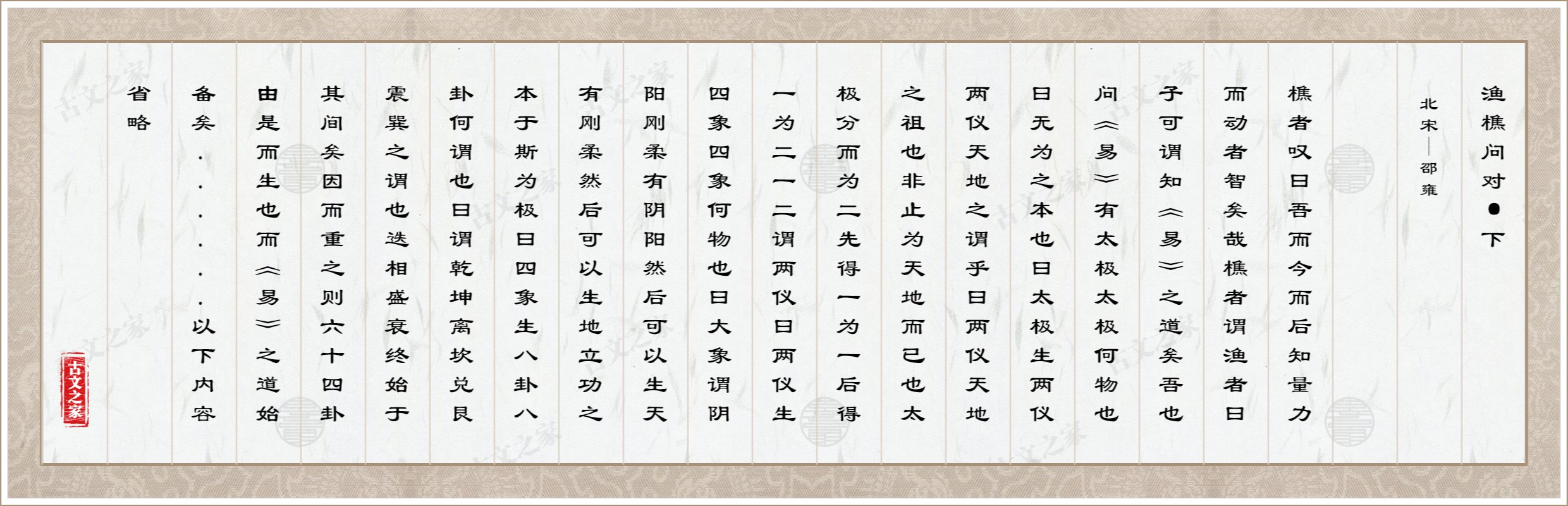对照翻译
樵者叹曰:“
樵者感叹道:“
吾而今而后,知量力而动者,智矣哉!”
从今以后,我知道做事量力而行才是有智慧的。”
樵者谓渔者曰:“
樵者问:“
子可谓知《易》之道矣。
你是知易理的人。
吾也问:
请问:
《易》有太极,太极何物也?”
易有太极,太极是何物?”
曰:“
答:“
无为之本也。”
无为之本。”
曰:“
问:“
太极生两仪,两仪,天地之谓乎?”
太极生两仪,两仪是天地的称呼吗?”
曰:“
答:“
两仪,天地之祖也,非止为天地而已也。
两仪,天地之祖,并非单指天地。
太极分而为二,先得一为一,后得一为二。
太极一分为二,先得到的一为一,后得到的一为二。
一二谓两仪。”
一与二叫做两仪。”
曰:“
问:“
两仪生四象,四象何物也?”
两仪生四象,四象为何物?”
曰:“
答:“
大象谓阴阳刚柔。
四象就是阴阳刚柔。
有阴阳然后可以生天,有刚柔然后可以生地。
阴阳可以生天,刚柔可以生地。
立功之本,于斯为极。”
一切事物的根本,于此为极点。”
曰:“
问:“
四象生八卦,八卦何谓也?”
四象生八卦,八卦是什么?”
曰:“
答:“
谓乾、坤、离、坎、兑、艮、震、巽之谓也。
八卦就是乾、坤、离、坎、兑、艮、震、巽。
迭相盛衰终始于其间矣。
是事物发展终始、盛衰的表现。
因而重之,则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,而《易》之道始备矣。”
两两相重,则六十四卦生出,易学之道就具备了。”
樵者问渔者曰:“
樵者问渔者:“
复何以见天地之心乎?”
如何见到天地的本性?”
曰:“
答:“
先阳已尽,后阳始生,则天地始生之际。
先阳耗尽,后阳出生。
中则当日月始周之际,末则当星辰始终之际。
则天地开始出现,变化到中期日月开始周行,变化到末期星辰显现。
万物死生,寒暑代谢,昼夜变迁,非此无以见之。
万物死生,寒暑代谢,昼夜变迁,事物以此相变。
当天地穷极之所必变,变则通,通则久,故《象》言‘先王以至日闭关,商旅不行,后不省方’,顺天故也。”
当天地运行到终了必然变化,变则通,通则久,所以《易》中象言‘先王到最后一日闭关,哪儿也不去’,是顺天行所故。”
樵者谓渔者曰:“
问:“
无妄,灾也。
无妄(卦名),属于灾。
敢问何故?”
是什么原因?”
曰:“
答:“
妄则欺他,得之必有祸,斯有妄也,顺天而动,有祸及者,非祸也,灾也。
妄是欺骗,得之必有祸,因此称妄,顺天意而行动,有祸秧及也不叫祸而叫灾。
犹农有思丰而不勤稼稿者,其荒也,不亦祸乎?
就像农民想着丰收而不去护理庄稼,其结果荒芜,不是祸是什么?
农有勤稼穑而复败诸水旱者,其荒也,不亦灾乎?
农民勤劳治理庄稼而遭水涝或干旱,其结果荒芜,不是灾是什么?
故《象》言‘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’,贵不妄也。”
所以《易》中象言‘先王以诚对万物’,贵于不欺骗。”
樵者问曰:“
问:“
姤,何也?”
姤(卦名),是什么?”
曰:“
答:“
姤,遇也。
姤是相遇。
柔遇刚也,与夬正反。
以柔遇刚,与夬卦相反。
夬始逼壮,姤始遇壮,阴始遇阳,故称姤焉。
夬始强壮,姤由弱遇壮,由阴遇阳,故称为姤。
观其姤,天地之心,亦可见矣。
观姤,天地的本性由此可见。
圣人以德化及此,罔有不昌。
圣人以德比喻,没有不明白的。
故《象》言‘施命诰四方’,履霜之慎,其在此也。”
所以《易》中象言‘姤施命于天下,就像走在霜雪之上,小心谨慎’,就在于此。”
渔者谓樵者曰:“
渔者接着说:“
春为阳始,夏为阳极,秋为阴始,冬为阴极。
春天是阳气的开始,夏天是阳气的极限,秋天是阴气的开始,冬天是阴气的极限。
阳始则温,阳极则热;
阳气开始则天气温暖,阳气极限则天气暑热;
阴始则凉,阴极则寒。
阴气开始则天气凉爽,阴气极限则天气寒冷。
温则生物,热则长物,凉则收物,寒则杀物。
温暖产生万物,暑热成长万物,凉爽收藏万物,寒冷肃杀万物。
皆一气别而为四焉。
皆是一气四种表现。
其生万物也亦然。”
其生万物也如此。”
樵者问渔者曰:“
樵着问渔者:“
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,何以知其然耶?”
人为万物之灵,是如何表现的?”
渔者对曰:“
渔者回答:“
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,耳能收万物之声,鼻能收万物之气,口能收万物之味。
人的目能收万物之色,耳能收万物之声,鼻能收万物之气,口能收万物之味。
声色气味者,万物之体也。
声色气味,万物之本,目耳鼻口,人人皆用。
目耳口鼻者,万人之用也。
物体本无作用,通过变化来表现作用;
体无定用,惟变是用。
作用也并不是表现在一个物体上。
用无定体,惟化是体。
而是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作用。
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。
由于物体和作用相交,则人和物的变化规律就具备了。
然则人亦物也,圣亦人也。
然而人也是物,圣人也是人。
有一物之物,有十物之物,有百物之物,有千物之物,有万物之物,有亿物之物,有兆物之物。
有一物、百物、千物、万物、亿物、兆物。
生一一之物,当兆物之物者,岂非人乎!
身为一物,就可以征兆万物。
有一人之人,有十人之人,有百人之人,有千人之人,有万人之人,有亿人之人,有兆人之人。
只有人,有一人、百人、千人、万人、亿人、兆人。
当兆人之人者,岂非圣乎!
生为一人,而能征兆他人,只有圣人。
是知人也者,物之至者也。
因此知道人是物的至尊;
圣也者,人之至者也。
圣人是人的至尊。
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。
物的至尊为物中之物。
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。
人的至尊为人中之人。
夫物之物者,至物之谓也。
所以物的至极为至物。
人之人者,至人之谓也。
人的至极为至人。
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,则非圣人而何?
以一物知万物、以一人知万人,不是圣人是什么?
人谓之不圣,则吾不信也。
人不是万物之灵,我不信。
何哉?
为什么?
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,一身观万身,一物观万物,一世观万世者焉。
因为人能以一心观万心,以一身观万身,以一物观万物,以一世观万世;
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,口代天言,手代天工,身代天事者焉。
又能以心代天意,以口代天言,以手代天工,以身代天事;
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,下尽地理,中尽物情,通照人事者焉。
又能上识天时,下晓地理,中尽物情,通照人事;
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,出入造化,进退今古,表里人物者焉。
又能弥纶天地,出入造化,进退古今,表里人物。
噫!
唉!
圣人者,非世世而效圣焉。
圣人并非世世可见。
吾不得而目见之也。
我虽不能亲眼见到。
虽然吾不得而目见之,察其心,观其迹,探其体,潜其用,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。
但我观察其心迹,探访其行踪,研究其作用,虽经亿万年也能以理知道。
人或告我曰:“
有人告诉我说:
天地之外,别有天地万物,异乎此天地万物。
天地之外,还有另外的天地万物,和此天地万物不一样。’
则吾不得而知之也。
而我不得而知。
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,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。
并非我不得而知,连圣人也不得而知。
凡言知者,谓其心得而知之也。
凡说知道的,其实内心并不知道。
言言者,谓其口得而言之也。
而说出来的,也只是说说而已。
既心尚不得而知之,口又恶得而言之乎?
既然内心都不明白,嘴又能说出什么?
以不可得知而知之,是谓妄知也。
心里不知道而说知道的,叫做妄知。
以不可得言而言之,是谓妄言也。
嘴说不清而又要说的,叫做妄言。
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!”
我又怎么能相信妄人的妄言和妄知呢?”
渔者谓樵者曰:“
渔者对樵者说:“
仲尼有言曰:
仲尼说的好:“
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可知也;
殷继承于夏礼,所遇的损益便可知道;
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
周继承于殷礼,所遇的损益也可知道。
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可知也。
其次继承周礼的,虽经百世也可知道。
夫如是,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!’
如此,何止百世而已!
亿千万世,皆可得而知之也。
亿千万世,都可以知道。
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,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,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,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,则舍天地将奚之焉?
人都知道仲尼叫仲尼,却不知道仲尼为什么叫仲尼。
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,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。
不想知道仲尼为什么叫仲尼则已,若想知道仲尼为什么叫仲尼,则舍弃天地会怎么样?
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,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,则舍动静将奚之焉?
人都知道天地为天地,却不知道天地为什么为天地,不想知道天地为什么为天地则已,若想知道天地为什么为天地,则舍弃动静会怎么样?
夫一动一静者,天地至妙者欤?
一动一静,天地至妙。
夫一动一静之间者,天地人至妙者欤?
一动一静之间,天地人至妙。
是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,谓其行无辙迹也。
因此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,是因其行没有辙迹。
故有言曰:“
所以有人说:“
予欲无言’,又曰:“
仲尼什么也没说,’又说:“
天何言哉!
天什么也没说!
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
但四时运行,百物出生。’
其此之谓与?”’
这些你知道吗?”
渔者谓樵者曰:“
渔者接着说:“
大哉!
大事中:
权之与变乎?
权力与变化谁重要?
非圣人无以尽之。
并非圣人不能讲清楚。
变然后知天地之消长,权然后知天下之轻重。
变化过后可知天地的消长,掌权之后可知天下的轻重。
消长,时也;
消长是时间的表现。
轻重,事也。
轻重是事物的表现。
时有否泰,事有损益。
时间有亨通与闭塞,事物有损耗与收益。
圣人不知随时否泰之道,奚由知变之所为乎?
圣人若不知随时间亨通与闭塞之道,又怎知变化之所为呢?
圣人不知随时损益之道,奚由知权之所为乎?
圣人若不知随时间损耗与收益之道,又怎知权力之所为呢?
运消长者,变也;
运用消长的是变化。
处轻重者,权也。
处置轻重的是权力。
是知权之与变,圣人之一道耳。”
因此权力与变化,是圣人的修行之一。”
樵者问渔者曰:“
樵者问渔者:“
人谓死而有知,有诸?”
人死后有灵魂存在,有这种事么?”
曰:“
答:“
有之。”
有。”
曰:“
问:“
何以知其然?”
如何才能知道?”
曰:“
答:“
以人知之。”
以人为知。”
曰:“
问:“
何者谓之人?”
什么样的叫人?”
曰:“
答:“
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,谓之人。
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的叫人。
心之灵曰神,胆之灵曰魄,脾之灵曰魂,肾之灵曰精。
心之灵称神,胆之灵称魄,脾之灵称魂,肾之灵称精,(中医认为,心之灵称神,肝之灵称魂,脾之灵称意,肺之灵称魄,肾之灵称精,这里有不同的见解,不知原文有误,还是有何深意,——译者注)。
心之神发乎目,则谓之视;
心之神表现在目,称为视;
肾之精发乎耳,则谓之听;
肾之精表现在耳,称为听;
脾之魂发乎鼻,则谓之臭;
脾之魂表现在鼻,称为臭;
胆之魄发乎口,则谓之言。
胆之魄表现在口,称为言。
八者具备,然后谓之人。
八者具备,才可称之为人。
夫人也者,天地万物之秀气也。
人,禀天地万物之秀气而生。
然而亦有不中者,各求其类也。
然而也有缺少某一方面的人,各归其类。
若全得人类,则谓之曰全人之人。
如果各方面都齐全的人,则称为全人。
夫全类者,天地万物之中气也,谓之曰全德之人也。
全人得万物中的中和之气,则称为全德之人。
全德之人者,人之人者也。
全德之人,为人中之人。
夫人之人者,仁人之谓也。
人中之人,则是仁人之称。
唯全人,然后能当之。
只有全人,才能得到仁人之称。
人之生也,谓其气行,人之死也,谓其形返。
人之生,在于气行。
气行则神魂交,形返则精魄存。
人之死,则是形体返还。
神魂行于天,精魄返于地。
气行则神魂交,形返则精魄存。
行于天,则谓之曰阳行;
神魂行于天,精魄返于地。
返于地,则谓之曰阴返。
行于天,称之为阳行,返于地,称之为阴返。
阳行则昼见而夜伏者也,阴返则夜见而昼伏者也。
阳行于白天而夜间潜伏,阴返于夜间而白天潜伏。
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,月者日之影也。
所以知道太阳是月亮的形状,月亮是太阳的影子。
阳者阴之形也,阴者阳之影也。
阳者是阴者的形状,阴者是阳者的影子。
人者鬼之形也,鬼者人之影也。
人是鬼的形状,鬼是人的影子。
人谓鬼无形而无知者,吾不信也。”
有人说,鬼无形而不可知,我不相信。”
樵者问渔者曰:“
樵者问渔者:“
小人可绝乎?”
小人能灭绝吗?”
曰:“
答:“
不可。
不能。
君子禀阳正气而生,小人禀阴邪气而生。
君子禀阳正气而生,小人禀阴邪气而生。
无阴则阳不成,无小人则君子亦不成,唯以盛衰乎其间也。
无阴则阳不生,无小人则君子不生,只有盛衰的不同。
阳六分,则阴四分;
阳六分,则阴四分;
阴六分,则阳四分。
阴六分,则阳四分。
阳阴相半,则各五分矣。
阴阳各半,则各占五分。
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时有盛衰也。
由此而知,君子与小人各有盛衰之时。
治世则君子六分。
太平盛世时期,君子占六分,小人占四分,小人不能战胜君子。
君子六分,则小人四分,小人固不能胜君子矣。
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各安其道。
乱世则反是,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,兄兄,弟弟,夫夫,妇妇,谓各安其分也。
世间纷乱时期正相反。
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兄不兄,弟不弟,夫不夫,妇不妇,谓各失其分也。
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、兄不兄、弟不弟、夫不夫、妇不妇则失其道。
此则由世治世乱使之然也。
这是由治世或乱世所造成的。
君子常行胜言,小人常言胜行。
君子常以身作则胜过空话连篇,小人常空话连篇胜过实际行动。
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,世乱则缘饰之士众。
所以盛世时期诚实的人多,乱世时期奸诈的人多。
笃实鲜不成事,缘饰鲜不败事。
诚实容易成事,奸诈容易败事。
成多国兴,败多国亡。
成事则国兴,败事则国亡。
家亦由是而兴亡也。
一个家庭也如此。
夫兴家与兴国之人,与亡国亡家之人,相去一何远哉!”
兴家、兴国之人,与亡国、亡家之人,相差的是多么的远!”
樵者问渔者曰:“
樵者问:“
人所谓才者,有利焉,有害焉者,何也?”
人有才,有的有益,有的有害,为什么?”
渔者曰:“
答:“
才一也,利害二也。
才为一,益与害为二。
有才之正者,有才之不正者。
有才正、才不正之分。
才之正者,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;
才正,益于身而无害。
才之不正者,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。”
才不正,益于身而害人。”
曰:“
问:“
不正,则安得谓之才?”
才不正,又如何成为才呢?”
曰:“
答:“
人所不能而能之,安得不谓之才?
人所不能做的你能做到,能不成为才吗?
圣人所以异乎才之难者,谓其能成天下之事而归之正者寡也。
圣人所以怜惜成才难,是因为能成天下事而又正派的人很少。
若不能归之以正,才则才矣,难乎语其仁也。
若不正派,虽然有才,也难称有仁义。
譬犹药疗疾也,毒药亦有时而用也,可一而不可再也,疾愈则速已,不已则杀人矣。
比如吃药治病,毒药也有用的时候,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用,病愈则速停,不停则是杀人了。
平药则常日而用之可也,重疾非所以能治也。
平常药日常皆可用,但遇重病则没有疗效。
能驱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,古今人所谓良药也。
能驱除重病而又不害人的毒药,古今都称为良药。
《易》曰:“
《易》说:“
大君有命,开国承家,小人勿用。
开国立家,用君子不用小人。’
如是,则小人亦有时而用之。’
如此,小人也有有用的时候。
时平治定,用之则否。
安邦治国,则不要用小人。
《诗》云:“
《诗》说:“
它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
它山之石,可以攻玉。’
其小人之才乎!”’
就是借用小人之才。”
樵者谓渔者曰:“
问:“
国家之兴亡,与夫才之邪正,则固得闻命矣。
国家兴亡,与人才的正邪,各有其命。
然则何不择其人而用之?”
哪为什么不择人而用呢?”
渔者曰:“
答:“
择臣者,君也;
择臣者,是君王的事。
择君者,臣也。
择君者,是臣民的事。
贤愚各从其类而为。
贤愚各从其类。
奈何有尧舜之君,必有尧舜之臣;
世上有尧、舜之君,必有尧、舜之臣;
有桀纣之君,而必有桀纣之臣。
有桀、纣之君,必有桀、纣之臣。
尧舜之臣,生乎桀纣之世,桀纣之臣,生于尧舜之世,必非其所用也。
尧舜之臣,生于桀、纣之世,则不会成为桀纣之臣,生于尧舜之世并非是他的所为。
虽欲为祸为福,其能行乎?
他想要为祸为福,可不是想干就能干的。
夫上之所好,下必好之。
上边所好的下边必效仿。
其若影响,岂待驱率而然耶?
君王的影响,还用驱赶去执行吗?
上好义,则下必好义,而不义者远矣;
上好义,则下必好义,而不义的人则远离;
上好利,下必好利,而不利者远矣。
上好利,则下必好利,而不好利的人则远离。
好利者众,则天下日削矣;
好利者多,则天下日渐消亡;
好义者众,则天下日盛矣。
好义者众,则天下日渐兴旺。
日盛则昌,日削则亡。
日盛则昌,日消则亡。
盛之与削,昌之与亡,岂其远乎?
昌盛与消亡,难道不远吗?
在上之所好耳。
都是在上好恶影响的。
夫治世何尝无小人,乱世何尝无君子,不用则善恶何由而行也。”
治国安民之时何尝无小人,乱世之际又何尝无君子,没有君子和小人,善恶又如何区分呢?”
樵者曰:“
樵者问:“
善人常寡,而不善人常众;
善人常少,不善人常多;
治世常少,乱世常多,何以知其然耶?”
盛世时代短,乱世时期长,如何鉴别呢?”
曰:“
答:“
观之于物,何物不然?
观察事物。
譬诸五谷,耘之而不苗者有矣。
什么事物不能表现出来,比如五谷。
蓬莠不耘而犹生,耘之而求其尽也,亦未如之何矣。
耕种之后有长不出来的,而逢野生物不用耕种就能长出来,耕种之后想要全部收获,是不可能的!
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,有自来矣。
由此而知君子与小人之道,也是自然而生。
君子见善则喜之,见不善则远之;
君子见善事则欢喜,见不善事则远离;
小人见善则疾之,见不善则喜之。
小人见善事则痛苦,见不善事则欢喜。
善恶各从其类也。
善恶各从其类。
君子见善则就之,见不善则违之;
君子见善事则去做,见不善事则阻止;
小人见善则违之,见不善则就之。
小人见善事则阻止,见不善事则去做;
君子见义则迁,见利则止;
君子见义则迁,见利则止;
小人见义则止,见利则迁。
小人见义则止,见利则迁。
迁义则利人,迁利则害人。
迁义则益人,迁利则害人;
利人与害人,相去一何远耶?
益人与害人,相去有多远?
家与国一也,其兴也,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鲜;
家与国一样兴旺则君子常多,小人常少;
其亡也,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鲜。
消亡则小人常多君子常少。
君子多而去之者,小人也;
君子多小人躲避。
小人多而去之者,君子也。
小人多君子躲避。
君子好生,小人好杀。
君子好生,小人好杀。
好生则世治,好杀则世乱。
好生则治国安民,好杀则祸国殃民。
君子好义,小人好利。
君子好义,小人好利。
治世则好义,乱世则好利。
治国安民则好义,祸国殃民则好利。
其理一也。”
其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钓者谈已,樵者曰:“
渔者说完,樵者感慨万分:“
吾闻古有伏羲,今日如睹其面焉。”
我听说上古有伏羲,今日好像一睹其面。”
拜而谢之,及旦而去。
对渔者再三拜谢,相别而去。
 《渔樵问对·下》全文注音拼音版
《渔樵问对·下》全文注音拼音版